撰文:庄礼伟 编辑:周小林
 此主题相关图片 此主题相关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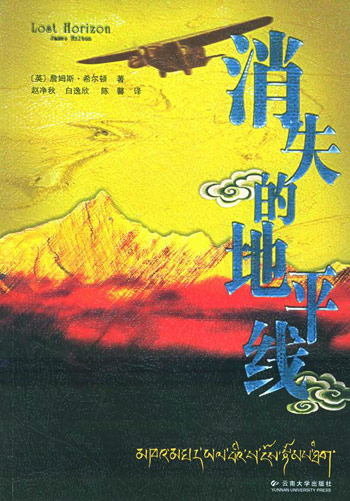
“香格里拉学”中的索隐游戏
“发现”“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的人,其主要理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从外貌到内涵都与《消失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的描述相吻合。把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硬生生地与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地点等同起来,这是索隐派的毛病。
在红学中所谓“索隐”,就是指试图发现《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都“真有其人、其事、其地”。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在论证“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这个“重要学术观点”时,其论证方法如下:小宛名白,黛玉名黛,粉白黛绿非常对称;小宛爱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黛玉善琴;小宛善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黛玉亦癖月,所以,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这便是“索隐”。
“香格里拉学”,自然无法与“红学”相提并论,不过“香格里拉”与“红楼梦”中若隐若现的“真相”,都吸引了许多索隐者。在红学方面,刘心武从秦可卿可人的身体和可疑的身世探究红楼“真相”,为索隐派再添新的震撼性“研究成果”。在“香格里拉学”方面,则存在一个庞大的“官产学”索隐联盟。
本人认为“香格里拉”是一个存在于虚无飘渺中的乌托邦,这与索隐派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对付索隐派的办法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接下来我也运起“索隐”大法,来寻找《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历险记的“真有其地”,进而证明“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这一观点,即便从索隐角度来看也不是最有说服力的。
索隐一:飞往“香格里拉”的线路与降落地点
本人依据的文本是在尼泊尔Thamel区书店里买到的《消失的地平线》英文本(Lost Horizon),以下将依次分析小说中所隐藏的各项“真事”,进而判断出“香格里拉”的“真实位置”。
根据小说中提供的航空资料和地理资料,笔者“索隐”如下:
【1】 飞往“香格里拉”航程的起点,是巴斯库尔(Baskul),此地疑似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当时阿富汗与印度是邻国,并且都受英国控制。阿富汗发生暴乱,英国人向英属印度(含巴基斯坦和印度)撤侨是很自然的事,而英属印度靠近阿富汗的最大边境城市正是小飞机要前往的白沙瓦(Peshawur,今属巴基斯坦)。从飞机航向来看,基本上是向东飞,而英属印度正是在阿富汗的东边。由此可判定:起飞地点是在阿富汗,并且是一个英国人比较多的大城市(很可能是喀布尔)。
康威等人登上小飞机后被劫持到“香格里拉”,起因是这一年5月的严重暴乱导致英国撤侨。而阿富汗在1919年5月发生反英大起义之后,同年8月宣布独立,这一“五月之乱”当然是令英国人难忘的,希尔顿可能借用了这一历史场景。
【2】飞机起飞的时间,则被安排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某年。小说中提到“香格里拉”喇嘛寺的图书馆中,有一批出版日期为30年代中期的新书。
【3】飞行路线。希尔顿在创作《消失的地平线》,心中可能有一张大致的飞向“香格里拉”的飞行线路图(他甚至可能在克什米尔附近坐过这种小飞机,所以能翔实地描述从高空中所看到的喀喇昆仑雪山)。依据小说中提供的资料,笔者重建飞行线路如下:
20世纪30年代中期某年5月20日上午10点整,这架小飞机从喀布尔起飞,向东偏南方向的白沙瓦飞行。但从“香格里拉”出来的负有寻找最高喇嘛接班人使命的飞行员(他冒名顶替上了这架飞机)把康威他们带到东北方向的克什米尔的荒凉地带,并着陆加油。小说中写到有一个帕坦人(Pathan)走过来帮飞行员转动螺旋桨,而帕坦人正是生活在克什米尔山区。
下午3点钟左右,飞机加油后又开始飞行。航向一直朝东,有时偏北一点。小说中说飞机大致沿着东西走向的印度河上游河谷飞行,巧的是,飞机必然经过“克什米尔的香格里拉”——拉达克(Ladakh)地区,而印度河上游的源头,就是最像“香格里拉地标”(卡拉卡尔雪山)的冈仁波齐雪山。可以说,小飞机加油后,就一直在“香格里拉”的氛围中飞行。
在沿印度河河谷飞行的途中,一个确切的地标出现了,这就是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世界第九高峰,位于现在的克什米尔巴方境内,印度河上游南侧。飞机沿河谷向东飞行,这座高峰当在飞机的右侧。而飞机的左侧(北方),康威他们看到的是一长列的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s)。由于飞机航向是朝东偏北,显示飞机将穿越喀喇昆仑山脉而飞向西藏的高原。
当暮色降临(大约晚上6点多),康威他们看到了另一个知名地标——K2(即乔戈里峰,喀喇昆仑山脉主峰,世界第二高峰)。当看到夜色中的K2时,康威推测这架小飞机加油一次可飞1000英里(1609公里),并且差不多已飞到这个距离了。1609公里能从哪里到哪里呢?从加油后经过的南迦峰算起,乃至从K2算起,朝东南、正东、东北方向最大航程可及的地方也只有不丹王国、拉萨、唐古拉山口、昆仑山的慕士塔格峰等地,断然飞不到大约2400公里之遥的滇西北,除非有一次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空中加油。这说明“香格里拉”的“位置”是有所限定的,是在拉萨以西的藏区。
【4】降落地点。夜里1点半,飞机着陆。小说中说,康威估计飞机已越过喜马拉雅山西段,进入了鲜为人知的昆仑(Kuen Lun)山区,他们的脚下,是世界上最高的极冷地带——西藏高原(Tibetan plateau)。小说中对降落地点的地貌描写,与高而阔的西藏高原相近,而与滇西北的横断山区差异较大。综合【3】与【4】,可知“香格里拉”是位于月球般荒凉的拉萨以西的西藏高原。
【5】小说末尾说“香格里拉”离它东边的汉藏交界处的“塔城府”(Tatsien-Fu,有人认为是稻城)有1100英里(约1770公里)之遥。无论“塔城府”是不是稻城,总之“香格里拉”与藏区东边的汉藏交界地区有1770公里的距离。那么,从川、滇的汉藏交界处向西1770公里处的地方是哪里呢?请大家把地图拿起来看吧,那里不正是藏西地区吗?
【6】小说末尾还提到康威从曼谷出发,向西北方向去寻找“香格里拉”。从经线看,云南迪庆州几乎是在曼谷的正北。而从10点半角度(即正西北方位)望去,正好是喜马拉雅山和藏西北的人烟稀少地区。这也是对“香格里拉”方位的一个确切指向。
【7】小说中还提到,“香格里拉”作为人类大劫难来临时的文明避难所,具备人迹罕至、极难到达、极难被发现的特点,汉藏边界的中甸或稻城都不具备这些特点,而藏西北的昆仑山地区倒是一个离各个人烟稠密区都很远的地方。
综上所述,飞机的降落地点(依据《消失的地平线》,从此地到“香格里拉”只需走大半天山路),很可能是西藏高原上、拉萨以西的某个地方;从航程和康威的观察来判断,很可能是藏西北的昆仑山区。
笔者无意为昆仑山区做旅游广告,但那里的无比荒凉与人迹罕至,确实适合于隐藏一个不想为外人所知的“香格里拉”。
索隐二:“香格里拉”中的“拉”
笔者在《“香格里拉”在炒作中的崩塌》中提到,“香格里拉”(Shangri-La)的“拉”(La)在藏语中是山口、山的通道的意思。因此,“香格里拉”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叫“香格里”的山口,它应当读成“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尽管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由希尔顿杜撰出来的词汇,但它仍然有相当的现实基础。在西方探险家关于克什米尔、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藏西高原的旅行记录中,有大量带有后缀“La”的地名,基本上都是指某某山口。在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之一,曾三次翻越昆仑山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所著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李述礼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藏语中,“Tso”是湖泊的意思,“La”是山口(李述礼译成“山头”)的意思。
如该书第411页:斯文赫定一行前往克什米尔的首府斯里那加尔(Srinagar)。途中徒步穿越危险的Sodschi-la。第423页:从克什米尔境内前往西藏,要经过5360米的Tschang-la。第425页:赫定到达Marsi-mik-la,并穿过雪山下荒莽的山谷;在前方,则有Lanek-la,从那里有一条到西藏的路。此外书中还有Sela-la、Schib-la、Ta-la、Kilung-la、Kore-la、Tam-lung-la等等大量的类似地名——“香格里拉”(Shangri-La)很有可能就是它们中的一员。在从克什米尔穿越喀喇昆仑到达藏西高原和昆仑山这一线,有无数这样的“La”(山口),那个隐秘的“香格里拉”,很有可能隐藏在这个地带的某个极为崎岖、偏僻的地方。
并且,在斯文赫定关于克什米尔、藏西高原的游记中,也记录了许多与“香格里拉”相似的景色:
第408-409页:斯文赫定从西藏返回印度,途经咸水湖班公错(Panggon-tso)。赫定说,这湖在它那庞大的岩壁间犹如一道雄伟的河谷,是地球上最伟大的风景之一,湖边山顶上有永久的积雪,山肩就像舞台的两翼似的突将出来,一座挨着一座地一直排列到很后面的西北方,色彩越来越淡。这些描述都让人想起《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蓝月山谷”——康威曾担心卡拉卡尔雪山的融水出口如果被堵住,那么“蓝月山谷”也将成为一个“峡谷湖”。
斯文赫定还提到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拜见“达齐喇嘛”的情景(第474页):房间里的陈设具有多元文化的内涵,而达齐喇嘛“至少照我们的观念看来,他不算完美,但我忘怀了这一层,因为我整个时间都为他的眼睛,他的微笑,他那伟大的澹静,和他那细弱的、几乎是颤栗的声音所迷惑。我们整整谈了3个钟头,谈到我的旅行,谈到欧洲、中国内地、日本、印度以及成千种别的事情”。这分明是康威觐见“最高喇嘛”时的情景!此外,书中有欧战的背景和对战争的厌恶,这也是康威与“最高喇嘛”交谈的一个主题。
书中第494页还有一幅喇嘛寺图,它与《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喇嘛寺简直一模一样:在山腰上矗立,下方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四周群山环抱。
在《西极探险——从叶尔羌到藏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鸣野译)一书中,赫定还提到:翻越喜马拉雅山的Zoji-la山口后,高度迅速下降,前面是黑绿色的森林、风景如画的村庄及其快乐的村民、泛着泡沫的河流及其轻盈、优雅的桥梁、村子后面银光闪闪的雪原以及那土耳其玉般的苍穹(第252页)。这种情景转换,也像康威一行翻过崎岖山口后看到“香格里拉”时的情形。
在《亚洲腹地旅行记》第526—528页,斯文赫定还提到地球上最灵圣的山——康林博刺(冈仁波齐)。这座灵山形状非常优美,像是“立在地基上的一个四面体”(这不正是金字塔的形状吗?),周围都是峭直的墙壁。它的峰顶盖上永久的冰和雪,溶水从峰缘注下,形成冒白沫的白色“新娘面纱”。在山谷上面,都是些花岗石,种种稀奇的结构,“使人以为看见了巨大的堡垒、墙壁和高塔”(这也酷似康威所看见的“香格里拉”喇嘛寺,它由“棱堡、院墙和宝塔”构成)。在该书第5-6页,还有赫定创作的险峻的高山通道素描图和金字塔形状雪山的素描图。
在西方知名度很高的赫定的这些文字和素描,希尔顿当然也很有可能看到。
至于更为广阔的风景,《亚洲腹地旅行记》第426页提到,当斯文赫定登上一个山峰时,雄伟的远景已是他辛劳的报酬,他认为这无疑是地球上最雄壮的风景之一:地球上最高的山涛所构成的一片汪洋包围着我们;喜马拉雅山的晶白雪顶在南面和西南面耸起。喀喇昆仑的首峰向西北和西南伸出。——这样的高原地平线上的“山涛”,正是康威他们在飞机上和着陆时看到的西藏高原的景象,这在滇西北横断山区是看不到的。
还是在第426页,斯文赫定有这样的描述:在荒莽的西藏高原,这里一根草都没有,回头仍可看见喀喇昆仑的高峰在铅板式的蓝黑色的云彩底下。它们间或被闪烁的电光所照耀,雷声在群山中荡过。——这不正是康威所看到的“香格里拉”的雷电之夜吗!赫定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狭长的)纵谷,纵谷上方有昆仑山山系中的一座“宝塔型的雪峰”,谷地里则有美丽的牧场。——这不正是“香格里拉”的地形图吗!
读过《消失的地平线》的朋友如果再看到斯文赫定上面的各段描述,一定会拍起桌子来!——希尔顿分明是在“抄袭”斯文赫定的藏西游记!换言之,“香格里拉”及其周边地区地貌的最主要原型,是斯文赫定游记中的从昆仑山到喀喇昆仑山之间的藏西!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的景观描写中,存在着一个像拍电影一样的“摄像视角”,这就是站在西藏高原上,扫视着高原地平线上连绵的雪山波涛和高原下方裂开的山谷,而“香格里拉”就像是在地下——从广袤的高原平视过去,“香格里拉”山谷自然就像在裂开的“地下”。这种视角与感觉在约瑟夫洛克的川西南—滇西北游记中是找不到的。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创造出“香格里拉”奇境的这本小说为什么叫做《消失的地平线》——地平线是指在藏西高原上看到的地平线,当康威他们走进高原下的裂谷,眼前是壁立的岩石,地平线也就消失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假定:希尔顿很有可能参考了斯文赫定等人在藏西高原探险时的记录,而“香格里拉”,按照 “索隐派”的“真有其事、其地、其人”的法则,很可能是在藏西高原上某个裂开的狭长的“纵谷”中。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在20世纪20年代用12种语言发表,而《消失的地平线》在1933年出版,希尔顿有可能读到迪庆派、稻城派推崇的约瑟夫洛克,更有可能读到名气更大的斯文赫定。
索隐三:“香格里拉”
在藏西昆仑山中
尽管本人仍然认为“香格里拉”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在地球上没有对应的存在,但如果“索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香格里拉”就在藏西昆仑山中。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有许多线索暗示了“香格里拉”的“真实位置”:
书中提到满洲女孩萝辰(Lo-Tsen)偶然进入“香格里拉”的经历。希尔顿写道:满洲皇族女子萝辰被许配给一位突厥王子,她前往Kashgar(喀什)去成婚,途中迷路而来到“香格里拉”。去喀什而又要迷路到藏区的话,一般是走塔里木盆地南线(经若羌、和田),因此萝辰她们很有可能在疆藏交界的昆仑山中迷路,进而来到“香格里拉”。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故事的叙述人拉瑟佛德(Rutherford)说自己也要去寻找“香格里拉”,他重点搜寻的地区就是极少有人敢于涉险深入的昆仑山区。在昆仑山外围,他遇到一位美国旅行者,后者试图穿越昆仑山,但是找不到道路,山口倒是发现了几个,但都高得难以攀登。拉瑟佛德接着说,这位美国旅行者在昆仑山地区的见闻与康威一行人的见闻“大同小异”。
此外,拉瑟佛德还曾到Yarkand(叶尔羌,即现在的莎车)和Kashgar(喀什)这些靠近昆仑山的地方打探“香格里拉”的消息(喀什和叶尔羌在斯文赫定的游记中也常被提及)。
这些情况都说明“香格里拉”与昆仑山有关。
在小说的末尾,希尔顿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干脆直接泄漏了他的故事构思的“原型”:那位曾在昆仑山区探险的美国旅行者,在战前的1911年与美国某个地理学会的几位同行在靠近昆仑山的地方,遇到一个中国人坐在由当地轿夫抬着的轿椅中,这个中国人能说流利的英语,并且热情地推介他们去参观附近的某座喇嘛寺,他甚至说他可以来做向导。这个出现在昆仑山附近、坐在轿椅中、能说英语的中国人,和康威他们在“香格里拉”附近遇到的坐在轿椅中、能说英语、邀请他们去“香格里拉”喇嘛寺的中国人Chang先生,几乎就是同一个人!
小说中还提到有人翻越天山来到“香格里拉”,这说明“香格里拉”在西藏西部的可能性极大。总之,书中有诸多线索都指向藏西昆仑山,可是同样注重索隐的“迪庆派”却总是视而不见。
当然,同时拥有高山、峡谷、草甸、喇嘛寺、垂直气候的地方有很多(如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西藏南部,以及横断山脉),希尔顿对“香格里拉”的想象与上述地方可能都有关系。但是希尔顿为什么要把“香格里拉”安放在藏西荒凉之地?这是大有深意的——只有离最近的现代商业文明至少有1770公里的地方,才可能是一个丝毫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一个极难被外界发现的人类文明的最后避难所。
笔者虽然在小说中追索出大量关于“香格里拉”就在昆仑山区的“证据”,但笔者并不情愿执著于这个“索隐”出来的“成果”(这个态度和“迪庆派”是不一样的,他们还要通过行政力量来“坐实”他们的“学术成果”)。身处广州都市红尘中的我,心想,乌托邦都只能在离人类社会、离想象者自己越远的地方,在人类越难以抵达的地方,才越有可能“存在”。
“香格里拉”的确切位置在哪里?答案仍然是3个字:不知道。也许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 |